现在的位置:主页 > 综合新闻 >
2021年度书评观察:从“被挤出期刊”到豆瓣“打(3)
【作者】:网站采编【关键词】:【摘要】:电影《天才捕手》( Genius 2016)剧照。 在今年8月,《书城》的一篇《诗人的萤火虫》 (作者:史凤晓) 在自然史中谈诗人如何理解萤火虫,从“自然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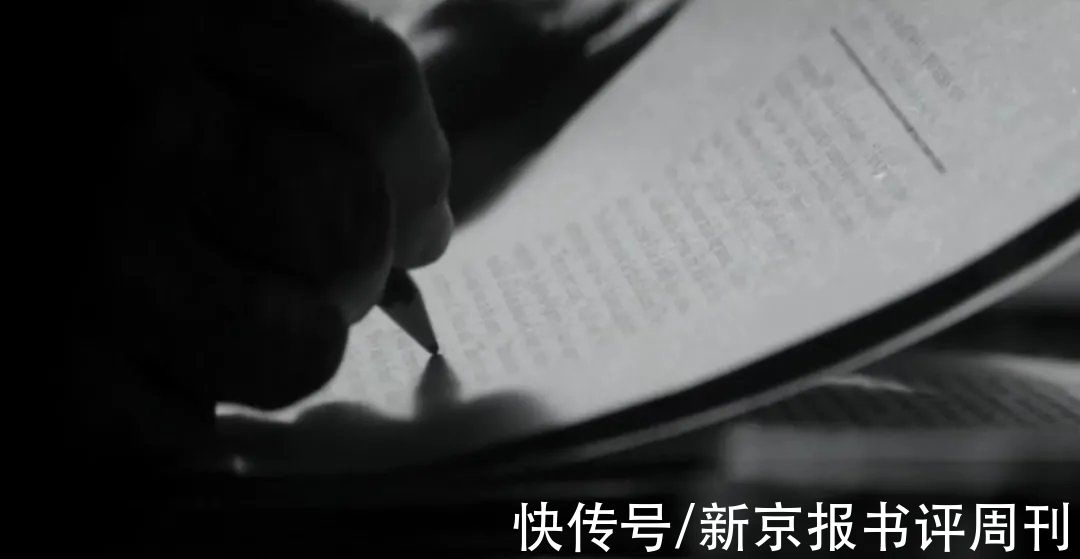
电影《天才捕手》(Genius 2016)剧照。
在今年8月,《书城》的一篇《诗人的萤火虫》(作者:史凤晓)在自然史中谈诗人如何理解萤火虫,从“自然”专门知识到诗歌,让人看到多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交叉后的魅力。在这一年,像这样的读书文章在《读书》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也有一些。它们的写法大多是从一个主题展开,融合多本书或多位思考者的知识。尤其在纪念沈昌文、李泽厚等老先生的若干篇文章中,我们读其中的书,也读其中的人和故事。另有读书文章,在阅读和引用外加入作者本人的一些实地观察,如《读书》4月号刊登的《后厂村路上的北京折叠》(作者:赵益民),对“城市密度”的反思给人以启发。
然而,真正稀缺的,其实是单论一本书的书评。我的意思不是指整篇文章只有一本书,而是下笔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探讨一个话题而找书,而是为了评书去找其他材料。所评之书是文章的中心。某种程度上,这样的书评更有挑战性。
这是因为我们都极其容易走进一种写作套路。譬如,将书的内容重述一遍,讲下成书或作者背景,再引用其他书的相关观点辅助论证,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全面的,却也是缺乏焦点的,无奈,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几乎就是一种套路。大多数单论一本书的书评都有这个问题。比如《书城》10月号评论段义孚《浪漫地理学》的《浪漫主义不是文学艺术的专利》(作者:苗德岁)就逐章讲述、评论。当然这篇书评依然能打动人,吸引人学习它的内容。我猜这是因为文章的写法是老派副刊的,信手拈来,关键处有点评,不刻意追求“深刻”。这是未过度专业化的写法,不会充斥着唐突的术语。用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·C.斯科特的话说,过度专业化必然导致知识多样性的枯竭。
在这一年,印象同样深的是《读书》9月号刊登的《从细微处看大关节》(作者:葛兆光),评的一本新书《图像、观念与仪俗》,作者的知识和写法自然都不必多说,书评也可以说是典范。可是,作者和所评之书的作者彼此熟悉。而很多好的书评竟然都有这样的特征,这或许是必然的。
一来,与学科专业化发展方向相反的是,越是专业,读者范围越是小,即便教师和学生的规模扩大,读者虽然多了,可增加的读者依然来自本专业。二来,越是追求专业素养的学者可能越是在评论书时小心翼翼,不会妄评非本专业、不了解的书。再加之,这还是一件不计入科研考核并且费时费力的事,去评论一本与自己不相干的书,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那么,问题就在于,在今天,如果纯粹是因为读到某本书产生了兴趣,人们有多大的意愿、有多少时间和好奇心去写一篇书评。我们接着去看网络。在过去,有书评写作欲望的多是职业书评人,而除了职业书评人,我们现在到网上,去逛豆瓣或刷短视频,也会看到多种书评内容和形式。
03
“吐槽”,在网上
爱读书的人对豆瓣图书条目不会陌生,条目下的短评和书评是读书者发表评论的方式,当然还有“打星”,而这也是一旦有争议,表现就最为激烈、最为直观的地方。前几年,有多本书在豆瓣条目上遭遇“一星运动”。在去年,饭圈的“养号”行为也让《记忆记忆》等书躺枪,从“五星”到“一星”,各种打法涌入其中。
而在2021年也有一例“一星运动”。3月16日,豆瓣网友“高晗”对一本名为《休战》的西语小说打两星评价,认为该书中文版“机翻痕迹严重……希望出版社至少找西语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这些名家”。有一位叫“Anito Anago”的网友向高晗所在的学校发去一封邮件,举报她严重不实的言辞给译者和出版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邮件要求高晗为此公开道歉。谁料这随即掀起一场反举报的“一星运动”,除了《休战》,其他支持译者的多位译者也一同被“一星”。这成为这一年豆瓣图书条目下影响最大的事件。由此展开的议题包括翻译标准、翻译稿酬过低等。和书评相关的,还是评论的自由度和标准问题,“机翻”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,纠缠不清,也分不出个高下。而其实,豆瓣图书条目是几个会有批评性书评的地方之一。
文章来源:《河北学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hbxkzzs.cn/zonghexinwen/2021/1225/558.html

